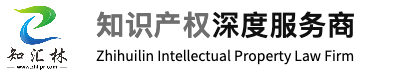版权搭台,剧目出彩
对舞台剧的表演权进行许可或转让,首次上线交易1026份表演权许可,将为市场增加1026场正版演出
对舞台剧的表演权进行许可或转让,首次上线交易1026份表演权许可,将为市场增加1026场正版演出……近日,北京市版权局、北京市版权保护中心、首都版权协会等共同举办了可信版权链舞台剧数字版权交易平台上线启动仪式,这标志着我国舞台剧行业从传统的创作、演出模式以及单一依靠票房的形式,通过北京市版权局数字证书和可信版权链平台,实现了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取得一份舞台剧数字版权表演权许可证书,就意味着享有一次正版的演出权益。
面临授权难题
舞台剧即呈现于舞台的戏剧艺术。舞台剧的剧情可以原创也可以根据小说、动漫、电视剧、电影等改编而来。舞台剧按内容可以分为喜剧、悲剧和正剧,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舞蹈、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近年来,我国舞台剧市场快速发展,涌现出了话剧《香山之夜》、歌剧《周恩来》、话剧《英雄儿女》、话剧《红岩魂》等一大批深受观众喜爱的舞台剧。而在今年1月8日,舞台剧《繁花》第一季上海站正式开票,仅仅3小时票房就突破200万元,由于购票者众多,服务器甚至一度瘫痪。1月15日,根据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孙甘露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话剧《千里江山图》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建组。该剧计划3月23日首演,由于深受观众欢迎,原定演出至4月7日,后将延长至4月14日。
第三方数据平台智研咨询发布的舞台剧报告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高质量的舞台剧深受消费者青睐。
舞台剧受欢迎的同时,也面临着版权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龙文懋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台上一出戏”涉及多种著作权和邻接权,比如戏剧脚本属于文字作品,上演舞台剧需要戏剧脚本著作权人发放表演权许可;参演人员拥有表演者权——这里要注意表演权与表演者权是不同的权利,前者是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后者是表演者的权利,属于邻接权;如果组织表演的单位将“整台戏”摄录下来,那么可能还涉及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如果将“整台戏”或者其中的片段上载到互联网上,则可能涉及著作权人、表演者、摄制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表演者、表演组织者还进行了二次创作,那么权利状况就更加复杂,正所谓“台上一出戏,台下许多权”。作品使用过程中涉及众多权利主体、权利种类,权利内容又是如此复杂,所以,要上演一台戏,处理背后的权利使用问题实属不易,众多的使用人尤其是那些个人等“小”主体恐怕难以独自应付。
对接市场需求
舞台剧著作权的应用主体广泛、分散,因而著作权交易、保护难度更大,加之权属不清、权利边界模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著作权保护和交易中存在着“两难”现象:一方面使用方想要获得著作权许可却难以找到著作权人,另一方面著作权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却维权困难。为此,业界进行了积极探索,可信版权链舞台剧数字版权交易平台就是其中的代表。
首都版权协会副秘书长、可信版权链全国运营中心主任宣宏量告诉本报记者,北京市版权局数字证书和可信版权链平台,打通了供给端和需求端,文化资源可以进入平台进行交易。生产端从平台购买文化资源加工提炼出素材再进入平台交易;剧目创作单位从平台购买进行演出或二次创作进入平台交易,并通过云端分发到消费端。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既是资源和生产的中介,又是生产和消费的中介,从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文化消费的全新体系。
不仅如此,在舞台剧确权方面,通过数据标识,平台为每份舞台剧数字版权证书的数据发放唯一身份证。以此次交易的表演权为例,由北京市版权局可信版权链进行确权,许可发行总量在46.1万份,预计实现舞台剧出品单位入表数字资产达2.7亿元,是我国舞台剧第一个数字版权资产入表的案例,推动舞台剧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我国文化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价值。同时也形成了法院、公证处、司法鉴定所、互联网平台等共同参与的数据治理生态,为文化数据提供基础服务。
对此,龙文懋表示,可信版权链将著作权交易数字化、格式化,使得“台上一出戏”涉及的版权交易可以快速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交易安全,无疑有助于促进交易、繁荣文化市场,同时也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权利,还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谓一举三得。同时,可信版权链具有权利主体明确、客体范围清晰、权利内容精确完整等优势,不但能够令应用方和权利人快速对接,而且能够准确识别作品使用的方式、路径,有助于在作品传播、二次创作的链条中明晰界定各个主体的权益和义务。
从“作品”到“产品”,可信版权链为舞台剧数字版权交易带来更多可能。